- 积分
- 134
- 注册时间
- 2010-1-22
- 最后登录
- 2015-10-24
- 在线时间
- 4 小时
TA的每日心情 | 无聊
2015-2-27 23:14 |
|---|
签到天数: 2 天 [LV.1]初来乍到
神探夏洛克
- 积分
- 134
- UID
- 353
 元宝 元宝- 659 个
 金币 金币- 257 枚
 热度 热度- 65 ℃
 魅力 魅力- 24 点
 贡献值 贡献值- 15 点
 玫瑰 玫瑰- 0 朵
|
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关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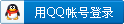
×
本帖最后由 暗泣 于 2010-2-27 16:14 编辑
小池真理子早期的小说毫无深度可言,那些个所谓推理小说,连《名侦探柯南》都不如。但从《独角兽》这部小说开始,小池笔下的人物开始深刻起来。
《独角兽》中的女主角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,文化水平不高,知识有限,头脑也不灵光,始终生活在社会的底层。她的头脑中就从来没有过清晰明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,日子过得浑浑噩噩。就这么一个看起来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、随波逐流的人,内心深处却并不是真的没有追求,她对现状并不是真正满意的。只是以她的头脑,并没有这种把自己追求的目标在头脑中清晰地整理出来的能力。她追求的是什么,是爱情?是幸福?是尊重?是金钱?她自己也没有概念。所以,她对现状的不满、她追求的欲望只能化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在身体里涌荡、冲撞,无处发泄,更无法表达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女人三十二岁,已经到了不能称为“女孩”的年龄。
但是,女人知道自己在男人的眼睛里,总是像一个小女孩。不知道是因为她体态轻盈,还是因为她身材窈窕,还是面颊胀鼓鼓的,使她的整个脸庞像一个小女孩,或是因为玩世不恭的举止会让人联想起少女的形象,总之只要女人在那里,男人们就会经不住引诱似的往她的身上靠,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
有人约她,拒绝的话嫌麻烦,于是便跟着去,男人要她做的事也都千篇一律。女人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惯,因为都是同一件事,好像盖图章一样。
仰天躺着,还不十分熟识的男人的手指和舌头在她的身体上爬行着,她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。她已经习惯于发出愉悦的喘息声。她已经学会按照男人的要求,为男人做出各种奇怪的姿势。
最后回家时,男人给她几枚一万元的纸币,她已经能默默地接过来,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。接钱时的手势也非常灵巧,内心里丝毫没有感到不妥。
然而,男人离开房间,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,女人也总是在想着同一件事。
就是,希望自己快快长大。
她希望自己年龄再大一些以后,既不是女人,也不是女孩,像一支用过的残烛似的,孤零零地站立着。
在镰仓的老房子里,住着一位版画家。他是女人打工的那家酒店里的常客。他正在寻找家政妇,于是便问女人:你,不想来试试?……
这是一家很低级的酒店,紧靠窗户底下流淌着一条臭水沟,酒店里臭气熏天,招牌上写着“高级居酒屋”,这是懵人的。
女人在来这家小酒店打工之前,已经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。她曾穿着工作服在一家小企业的总务科干过,但那种工作不合她的脾性,她打过的零工大多与饮食店有关。
有位客人一边喝着烧酒一边将手指伸进口腔里,用指尖剔着牙缝里的烧鸡渣滓。这样的客人会和版画家凑在一起,这种组合总是让人难以置信。
女人与这位客人也曾几度共眠,也许因此更会有一种不和谐感。
客人经营着一家不动产公司,在做旧房子的中介时,认识了那位版画家。版画家有着一种艺术家的气质,很难侍候,但一旦遇到现实问题,便会束手无策。这位客人很爽快地接受了他的求助,介绍业者为他割院子里的杂草,还为他修缮旧房,这样一来二去,虽说关系还不是十分密切,却也已经心思相通了。
据这位客人说,版画家看上去不那么有钱,单身生活,需要有一个能帮助他料理家务的人,他曾经向这位客人打过招呼,说如果有信得过的人,希望能介绍一个……
那个人,他有多大岁数了?女人问。
“这个嘛……大概有五十岁了吧。”
“夫人和孩子,有吗?”
“已经分居了呀!为什么分居,我不知道。那位先生,你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。不善辞令,没有必要就不会开口说话。平时很少有笑脸,所以有时还怀疑他是不是在生气,不料却也不是生气。嘿,人们说的艺术家,也许都是那副模样吧。”
“住在他家里?”
你想?客人脸上忽然绽开了贪色的笑容:“是钟点工,是钟点工啊。或许,你觉得还是住在那里,陪着睡觉好?嗯?”
女人朝客人轻轻地瞟了一眼,有些看不起他的样子,嘴里轻轻说了一句:“混蛋。”于是,客人抽动着咸鳕鱼子似的嘴唇,越发色迷迷地笑了。
女人居住在大船。说起镰仓,离女人的住宅很近。客人说那位先生是搞版画的,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,女人还不十分清楚。在她的脑海里,只能够想象出在幽静的画室里孤寂地工作着的、脸色苍白的中年男子的形象。
为难侍候的艺术家打扫房间、做饭、修剪院子里的草,此类事情可以轻而易举地应付过去。如果说他这个人沉默寡言,那就更求之不得了。
陪着满嘴荒唐话的男人,为他烫酒,面对男人下流的玩笑话,还要温顺地赔笑脸,不觉时间飞逝,等到清醒时,霓虹灯已经光怪陆离了,然后就是躺在廉价旅馆的床上。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,不知道过了多少年,女人早已经腻味了。
渐渐地,女人想要过平静安稳的生活了。纵然那位版画家向自己伸出手来,也只不过是如此,这正中下怀。如果对方是那么喜欢文静的男人,女人甚至觉得在佣金中加入睡觉费也无妨。她对那样的事已经能淡然处之了。
这时,女人才第一次发现自己对这臭水沟里臭气与酒气混杂在一起的气味,从心底里感到厌恶透了。
试试看吧。女人说道:“不过,那位先生,他同意我去吗?”
“我去说说看吧。”客人一口答应, “岂止是同意,也许会垂涎三尺呢。”
“你,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
你知道我说的意思。客人诡秘地一笑,小声说:“可是今天夜里呢?我们已经有很久……怎么样?”
女人只是厌恶地蹙起眉头,没有回答他的话。随便吧。那样的事情,全都是顺其自然的。
就像流动着的水那样,顺其自然地生活着。女人心里暗暗地想,今天夜里还是那样吧。
女人没有接受过正统教育。她没有想赚钱、想和有钱男人结婚之类催人奋进的志向,与为了某种目标而生存的生活方式也毫无缘分。
女人总认为原因在于自己的家庭不好。她曾经诅咒过自己的父母。然而,近来她也不去想那样的事情了。
女人心里想,自己即使接受过与别人同样的教育,也会对社会上的事漠不关心的。她不喜欢看报,也很少看电视新闻,她根本就没有听音乐、欣赏绘画、观赏电影之类的乐趣。她记得自己手上最后一次捧着称为“书”的东西,离现在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事了。
然而,女人从很早的时候起,就开始注意到自己内心深处有着静静的、然而却是狂澜般的风暴。风暴从她懂事的时候起就开始了。因为在内心如同狂澜一般的时间已经很长了,所以女人有时猜想,这样的话,自己大概会生出一个狂野的孩子来。
然而,女人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现自己这样的感觉。女人不善于表述,不会把某种感动、喜悦的心情或郁闷的情绪变成语言表达出来。
因此,在女人的情绪中,长期郁积着无法用语言表现的情感,而且越积越多,无处发泄,有时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动弹。
女人不会发泄自己的情绪,只好依然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着,从来不表露自己的心迹。她的脑海里从来就没有“这样下去行不行”之类的不安。
只要有男人向她伸手,她就接受。和男人一起睡到天亮,起床,再迎来黑夜。这样的生活,只要默默地接受,就能平静地过下去。没有必要去回顾它,已经过去的日子只是如同死了一般。
因此,在版画家的家里帮佣的时候,即使走进画室,面对着版画家雕刻的许多作品,女人的脑海里也浮现不出任何话语来。
事实上版画家制作的版画都非常雅致。正在制作中的版画暂且不说,已经完成的版画都非常精美。
画室里淡淡地倾洒着冬日的阳光,四周染着柔柔的白色。在这白色的外面,隔着窗玻璃的院子里,竖立着冬天枯萎的树木。
女人伫立着一动不动,她的全身笼罩着某种无法言状的厚实的感动。也许可以用“漂亮”、“真美啊”之类的语言来表现,但女人保持着沉默,一句话也不说,她在心里一个劲地告诫着自己:我只是一个女佣。
版画家也沉默着。他从来不会回过头去思考那种幼稚的情愫。这里是我工作的场所——他只是这样硬逼着自己。
是硬逼着自己……这就是女人对版画家的最初印象。
他既不是愤怒,也不是在表现自己的不悦,只是用冷冰冰的目光,像冷水淌过似的眺望着走过他眼前的人。他有着一种忽然要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内心里、紧紧地关上心扉的感觉。
听说他有五十岁,但外表看起来还稍稍年轻些,可以说估计不出他的年龄。
女人在没有见到他之前,头脑里想象出来的,是艺术家类型的苍白瘦削的身材,不料他长着厚实的胸脯,手臂上肌肉发达,因此,沉默寡言反而使他有着一种威严感。
女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与妻子分居,孤苦伶仃地独自住在镰仓谷户的一个角落里。看起来他也没有情人,用不着害怕被妻子知道。打来的电话,一般都是画廊或与工作有关的人,版画家甚至讨厌去接那些电话——他让女人接电话应酬。
也没有朋友来访。在投递来的邮件里,没有一眼就看得出的私密信件。
版画家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关在画室里,有时也跚跚地出去走一圈,他称之为“散步”。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回来,再次把自己关在画室里。
正儿八经能称为“吃饭”的用餐,一天只有一次。到了傍晚,他坐在女人准备好的饭菜前喝酒,女人说“我这就回去了”,他“呃”地点点头。每天就这么一句话。
版画家从来没有向女人流露出贪婪的目光,或者有过好色的举止。岂止这样,在他的眼里,那里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。
版画家不正眼看女人一眼,也不和女人讲话。偶尔女人说“今天天气真好”,他也只是点点头,不作回答。他要女人为他沏一杯咖啡到画室里,女人送去时,他头也不抬,只是说一声“谢谢”。
版画家养着一只猫。是一只全身雪白的大猫,名字叫“洁白”。猫很可爱,只是眼睛乌黑,仿佛凝聚着幽暗中的墨黑,还带着湿润。这只猫与其说是可爱,还不如说和它的主人一样,有些硬逼着自己,给人冷冰冰的印象。但不可思议的是,它对女人很亲近,女人叫它一声“洁白”,它就会靠上前来。
按照版画家的吩咐,给它喂食、换水,在洗手间的地上给它换砂,这也是女人的工作。
猫是不允许进画室的,所以版画家工作的时候,它就偎靠在女人的身边睡。女人在厨房里洗鱼剖肚,它就倚靠在她的脚边,“咪咪”地高声叫唤。
渐渐地,猫甚至愿意爬上女人的膝盖了。这白色的动物,像一个肥胖的婴儿那么沉重,女人马上就喜欢起它的重量了。
女人去版画家帮佣,已经有两个月了。
三月底一个风和日暖的寂静的下午,在准备晚饭之前,女人走到院子里,陪着猫玩耍,版画家从画室里走出来。
女人不知道版画家在身后看着,她抚摸着猫的背脊,和猫说着话。
版画家对女人说道:“你是第一个啊,‘洁白’这样亲近你。这只猫,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亲近过。”
女人听到版画家的说话声,感到有些意外,马上站起身来,一边拿围裙揉着手,一边只是怏怏地说了一句:“是吗?”
女人知道应该再说些其他什么话,比如“我很高兴”啦,“我很荣幸”啦。
然而,女人不习惯那样的措辞。无奈,她只好不说话,于是版画家朝女人望了一眼。令女人没有想到,那是一种随和的目光。
远处,栗耳短脚鹎在啼叫着。女人从版画家的身边穿过去,脱去脚上的拖鞋,走进了房间。
版画家很亲密地把猫抱到膝盖上。这样的举动,在他是很难得的。他抱着猫,在日光室里的藤椅上坐下。那是一间小小的日光室。猫开始在嗓子眼里发出“咕咯咕咯”的声音。
“你知道独角兽吗?”
女人正在收拾居室桌子上的报纸,她回过头来,眨巴着眼睛。
独角兽?——这句话,她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她心里在想,也许是外国的……中国一带的食物名字。
“在这里,”版画家抚摸着猫,用手指了指猫的头,“是头上长角的动物。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动物。这种动物是想象出来的,只出现在神话里。就像小马那么大吧,是白色的。脑袋和身体都像马一样,下颚像山羊似的长着白色的胡须,头上长着一只长长的角,笔直地伸着,很美丽的。”
女人点点头。她的头脑里浮想起孩子时在哪个牧场见到过的白色小马。
“那种动物很难驯服。别看它那样,脾性可暴躁了,有时还会咆哮。不过,只有一个是例外,就是它只对纯洁的少女很温顺。它对清纯的处女撒娇,偎靠在她的膝盖上。独角兽就是有那么可爱。关于独角兽的绘画留下了许多,光看看就很有趣。”
版画家说到这里,把抱在膝盖上的猫放在地上,脸上微微地聚起笑意,望着女人。女人第一次看见版画家这样面带笑容。
“‘洁白’简直就像是独角兽。它只对你一个人温顺,只被你一个人驯服。”
女人感觉到自己的耳根变得红热起来。
“你这么说……我不是什么处女。”
“我没有这样问你呀!”版画家毫无表情地说道,“我说的,是猫。”
女人伫立着低下头,紧紧地握着双手,望着修剪得很短的指甲。
“我也有过处女的时候……但是,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。现在,我已经忘了。”
“人人都是那样的吧。”
“我……很脏。”
“呃?”
“脏了就死心了。再怎样脏,也都是一样的,而且我和男人……”
女人说到这里,闭上了嘴。女人有着一种悲凉的情绪,心想自己大概说得太离谱了吧。
但是,版画家并没有在意她的想法,依旧坐在那里,平静地说道:
“我说的纯洁,不是那种意思。有的女人,即使与成千上百个男人睡过觉,也完全能保持自己的纯洁。与此相反,有的女人虽然只跟随一个男人,却也是浑身沾满现实生活里的污垢,恶浊熏人。幻想中的独角兽,正因为有着一种分辨那种女人的能力,所以才能够一直活在神话里。”
女人抬起头来,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版画家。她感到版画家的话很难理解,但又朦朦胧胧地能听懂他在说什么。
他是在教我什么深奥的事理,是在告诉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东西——她这么想着。
猫无声地走过来,把柔软的身体偎靠在女人的脚边。
“你瞧!”版画家说着,微微地笑了。
那是一种令人备感孤寂的微笑。
但是,女人感觉得到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,内心充满着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幸福感,她也笨拙地露出了微笑。
到了四月,女人有时也和版画家一起坐在桌子边用晚餐。
并不是版画家提出希望她一起吃饭,而是在帮佣着的时候,版画家开始有事无事和她说话,女人专注地听着,随着时间的流逝,最后自然而然地“如果会喝的话就一起喝吧”,于是便坐在一起用餐了。
版画家用平静的语调,向女人诉说着绘画、诗歌和小说,还说起在国外发生的、女人不太了解的事情,以及遥远的宇宙,有时还说起电影和话剧,还有音乐。
她觉得多听听版画家的话有好处,有很多话她听着也是一知半解。尽管如此,她总是非常入迷地听着版画家的絮叨。
版画家叙说时的语言,会一直渗透到女人的内心深处。但是,无论版画家使用什么样的语言,语调里总能感觉到冰凉凉的水在哗啦啦地流淌的悲哀。
那是一种无可言状、让人不知所措的悲哀。女人心里想,他为什么会这么悲凉呢?越是这么想,就越是觉得版画家不停地叙说着的语言,每一个词语都显得孤零零的,让女人感到极其忧伤,忧伤得难以自制。
在这样的生活中,不知不觉地到了太阳迟迟不落的季节,院子里充满着花儿的馨香。在风止雨霁的晚上,在附近流淌着的水渠边,传来青蛙的喧嚣声。
有时,女人到了晚上也不想回家。在伸手想斟酒却冷不防碰到版画家手指之类的时候,女人有时也会感觉到一阵麻痹似的愉悦。回家独自躺在被窝里,女人会产生一种幻想,幻想着自己被版画家抱在怀里。
我喜欢上他了?女人心里想。
女人从来没有过恋爱之类的感觉。平时总是男人情急慌忙地要求做爱,她只是有求必应。喜欢还是讨厌,痴迷对方还是被男人迷上,如此之类的情感,对女人来说,是一个未知的世界。男人与女人,就只是肉体与肉体的接触。
面对这样的女人,版画家叙说的语言变得更加丰富,语调更加充满着悲哀。有时能感觉到他不是在对着女人说话,而是在对着自己诉说什么。
词语在静静地、静静地流淌着。流逝的时间在词语的间隙发出潺潺的声响消失了。与版画家度过的夜晚是丰满而又让人憋得喘不过气来。
在叙说的过程中,版画家时而突然停住话头,流露出带着阴影的表情,目光凝视着空间的某一点。每次,女人都想要探找他目光前端的某种东西。
版画家忽然抬起头,用凝聚着哀伤的目光注视女人。女人知道他的瞳子里映现出来的,不是她的影子。正因为知道,女人也直率地注视着版画家。
在目光交织的隙缝间,羽虫在飞舞着,小小的飞虫发出“咿咿”的扑翅声,仿佛在呼唤:我才是现实。
那年五月,版画家用手枪击中太阳穴自杀了。
女人与平时一样,快到中午时去版画家的家里,窥探画室时,发现版画家脑袋打飞了,倒在地上。
画室的一面墙壁上溅满血迹,让人联想起紫酱红色的美丽绘画。
版画家没有留下遗书。警察来了解情况,女人颤抖着说:我什么也不知道。
版画家的妻子和儿子从东京赶来了。妻子有着奇怪的体型,面孔很小,像母鸡似的,惟独脸部和腹部凸出。儿子长得瘦削,二十二三岁,也许是在哪家公司里当业务员,穿着深藏青西服,怀里抱着黑色手提公文包。
两人都根本没有走进画室去的意思,只是在居室里抽抽嗒嗒,坐立不安。
你是谁?妻子问女人。
我是帮佣的家政妇。女人回答。
妻子露出厌恶的表情望着女人。这是一副轻蔑的表情。
什么自杀!妻子咬牙切齿地说道,后面又吐出了一句:有这么烦人的!
妻子的眼睛里有流泪的痕迹,但这不是悲伤或气愤或惊讶的眼泪,只能看作是冷不防被卷入天灾人祸时的眼泪。
女人把版画家养着猫的事告诉妻子。在警察进出的繁忙当儿,它不知去哪里了,但早晚会回来的。女人问妻子怎么办才好啊。
妻子回答说:猫这样的东西,我们不能领回去收养,我讨厌动物,何况这猫是丈夫自己要养的。
但是,如果不去管它,会变成野猫的。女人说道。
妻子催促着儿子去了走廊,两人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。不久妻子返回来,把用薄纸包着的小纸包递给女人,说是喂养猫的钱。
女人转过脸去,没有接受。妻子马上把纸包收了起来,只是说了一句:拜托你了。
白猫没有回来。女人久久地等着它,但是它没有回来,简直就像为了悼念主人的死亡而去冥冥的远方送葬了。
女人每天用她原来帮佣时配的钥匙去版画家的家里。因为她觉得,万一猫突然回家,家里却没了人的气息,这太可怜了。
版画家的妻子说,房子必须到夏天才能够打扫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也许是怕麻烦。
到夏天之前,房子就这么扔着没人居住,所以水电煤全都中断了供应。因此,女人不管什么时候去,房间里都显得很昏暗。因为无法烧水泡茶,女人去时还带着小瓶矿泉水。她心里想,如果猫回来的话,就和它分着喝。
版画家开枪打脑袋自杀的画室,业者已经重新给墙壁涂了漆,变得很整洁了。她想起妻子说过,不能每次来整理房间都看着那满是血迹的墙壁。女人心想,如果换了她,她决不会那么做的。
那些血迹非常美。小小的、细如针尖的众多红点,就像冷不防被强风刮着横向散过来似的,宛如甜蜜的石榴果汁。女人心想,这是版画家在这世上最后留下的一幅最美丽的作品。
开始的时候,女人只是白天抽空来一趟,看看猫有没有回来。她吹着口哨,咋着舌头,呼唤着猫的名字,在房子的四周不停地探寻着。
厨房门的下边开着一个小洞,供猫自由出入。女人把盛猫食的盆子放在厨房角落,每天换上新的食饵。
但是,每天这么重复着,女人开始隐隐觉得,猫有可能趁她不在的时候回来。她只要把食饵放着,猫能回来吃到,也许就可以活下去。但她觉得,如果那样的话,猫会很可怜的。
不久,女人开始在房间里等猫了。等两个小时,三个小时……有时也在房间里待一个下午。
她丝毫也没有感觉到这房间里不久前还死了人。女人没有感到害怕。房间里漂浮着的静穆,与以前没有丝毫的改变。她仿佛觉得,此刻画室的门静静地打开,版画家从里面走出来,将手臂伸进轻薄的外套衣袖,脸上毫无表情地说要出去散步。
版画家平时的生活状况,版画家的忧伤,依然清晰地留在这房间里,也许只是时间的轴心稍稍有些倾斜罢了。
即使在房间里,也没有事情可做。女人只是默默地、呆呆地坐着,望着院子。
女人想起版画家对她诉说的每一句话。“回想”变成了留给女人的惟一的喜悦。
女人屡屡在头脑里浮现的、而且不厌其烦地回想着的,是有关独角兽的话。
女人清楚地记得版画家向她说起独角兽时那宁静的表情,沉稳的面容,微微露出笑意的嘴唇的蠕动,注视着她时眼睛深处凝聚着的小小的光亮。
开始下雨了。昨天、前天都下雨,还以为雨要停,不料又下起来了。是像梅雨季节似的哗哗的雨帘。
还只是傍晚,四周却已经有些昏沉。院子里笼罩着薄雾似的暮霭,仿佛流淌过去的淡淡墨汁。
传来雨滴敲打树梢和茂盛的草叶的声音。雨滴滋润着泥土,泥土散发着清香,清香里混杂着树液和果实的馨香。
我在等待什么?女人渐渐地不明白起来。是白猫?还是独角兽?抑或是版画家?
女人仿佛觉得在雨幕下的院子深处,在带刺的山楂丛中,白色的、美丽的、长着一只角的幻想中的动物,眼看着就会出现。女人觉得,随着独角兽的出现,版画家也一定会回来的。
女人觉得自己的心灵非常清新,清新得十分忧伤。
女人只是一个劲地等待着。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