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积分
- 363
- 注册时间
- 2010-2-9
- 最后登录
- 2016-3-27
- 在线时间
- 25 小时
TA的每日心情 | 无聊
2016-2-21 21:44 |
|---|
签到天数: 17 天 [LV.4]偶尔看看III
水晶金字塔
- 积分
- 363
- UID
- 515
 元宝 元宝- 1254 个
 金币 金币- 232 枚
 热度 热度- 128 ℃
 魅力 魅力- 55 点
 贡献值 贡献值- 73 点
 玫瑰 玫瑰- 0 朵
|
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关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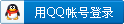
×
断指余波
一、不可思议
这一幕小小的活剧,当时曾给予我一种恐怖和憎恶的刺激。这刺激残留的印象并不因时间的间隔而淡漠。这时我握笔记叙,我的周身的肌肉还禁不住粒粒地起栗。
事情发生在我和佩芹结婚那年的秋季。婚后,我已和霍桑分居,但我在从事着作的余暇,仍不时和霍桑往来。
有时候霍桑逢着疑难案件,常特地约我去相助,我也仍旧跟着他往来奔波,直到案事了结,才重新回复我的文字生活。
那天下午,我因着我佩芹的弟弟—小名叫铭文的——高佩雄,在我家里吃饭,我陪他多喝了几杯酒,脑子里有些儿昏沉沉,就定意搁一搁笔,休息半天,乘空去瞧瞧霍桑。我离家时,佩雄还和他的姊姊在楼上谈话,没有回医校里去。
我的新寓在西门,换了两部电车,约摸费了三十分钟光景,才到爱文路我们的旧寓。
霍桑不在寓中。据施桂说,他不久就要回来,就开了办事室门,让我进去。
办事室中的景况还是老样子。书桌上的书报依然不大整齐。一只胆瓶中插着一枝白蜀葵,旁边的一只瓷盆中嗨有半段切好的荡藕。我取起来嚼了几片,又从烟罐中抽出一支白金龙,走到窗口的一只藤椅边坐下来,烧着了烟,缓缓地吐吸。
这时我虽然作客,但楼上还有我的床榻,我不时也住在这里,差不多还有一部分主人的资格,故而丝毫没有客气和顾忌。窗槛上摊着一本书,是一种研究人类血液的着作。我取过来读了几行,觉得没有小说那么有兴味,就丢过一旁。我默默地吸烟养神,约摸吸到半支,正自有些不耐,猛听得门铃声响。我忙从藤椅上立起来。霍桑回来了吗?不是。我记得我进来时没有下闩,若是霍桑自己,何必按铃?脚步声非常急促,越发不像霍桑。砰的一声,室门开了。走进一个人来,果真不是霍桑,却是我的妻弟高佩雄。佩雄那年刚十九岁,在上海医专二年级。他的身材不十分高,穿一套灰色哗叽西装,白衬衫,蓝领带。
他的略带苍黑的脸上有一双活泼的眼睛,面貌挺秀不凡。那时他将草帽拿在手中,两目大张,嘴唇也开而不合,呈现以种惊慌的颜色。
我怔一怔,急忙问道:“铭文,你还没有回学校里去?”
他摇了摇头,不开口。
我愈觉惊疑。我记得我离家时他还在楼上。此刻他为了什么事赶来?又为什么有这种状态?莫非佩芹有什么急病?或是有其他的变故?
我又问道:“佩雄,为什么这样子?可是我家里出了什么岔子?”
佩雄忽走近我些,低声答道:“不是,不是……我——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!……真是不可思议!”
我瞧着他的脸,答道:“哼!你又要来闹玩?”
佩雄忙挥挥手,正色抢着说:“姊夫,……别弄错。这不是闹玩的事。你瞧,这是什么?”
他急忙从他的外褂袋中摸出一样东西,承在手掌中,送到我的眼睛面前。我不由不倒退一步,骤然间感到恐怖和憎恶。
那是一枚从人手上割下来的指头!断指的颜色非黄非黑,我真描写不出,只可说是一种刺目的死色。那断割的一端又另有一种黝黑的猪肝似的颜色,更觉得可憎可怕。
我皱着眉峰,问道:“这东西你哪里来的?莫非——”佩雄把断指放在书桌上,接嘴道:“姊夫,别心急,我说给你听。刚才你出来以后,我和姊姊谈了几句,我也就回校里去。我坐的是第五路电车,到南京路口下车,预备换三路电车往肋板厂桥。谁知我第二次上车以后,买了票子,把手插在这袋里,忽觉得袋中有什么冰冷的东西触我的手指。我摸出来一瞧,就是这一枚可怖的断指。姊夫,你想我怎能不惊奇?故而我急急地赶来看你,请你或霍先生解释一下。”他摸出一块白巾来抹他的额汗,又向室的四隅瞧瞧。“霍先生呢?是不是出去了?”
我不即回答,又仔细瞧瞧他的脸。他的颜色果然非常庄肃,还有一种急于求解的神气。
我沉吟了一下,答道:“铭文,别慌。我看这东西一定是你的同学们偷偷地放在你的袋里的,目的无非和你开开玩笑。你们不是正在实习解剖吗?”
高佩雄连连摇头道:“不是。我起先也这样想。但是我还没有回到校里,这理解当然不能成立。”
“怎知道不是你在早晨离校以前,他们已经把这东西偷放在你的袋里?只是你自己没有觉察罢了。”
“也不是。我在你家里吃午饭时,曾把这件外褂脱下来。那时我怕袋中有东西掉落,曾在袋里摸过一摸,并没有什么。不但如此,我从你家里出来,上了五路电车,也曾将车票塞在这袋里,也明明没有这个东西。”
他的语气很坚决。他瞧瞧桌上的断指,又瞧瞧我,呼吸似乎很短促。我仍保持着镇静,企图找出一个头绪。
我说:“铭文,你姑且坐下来。慌张没有用。”
他果然坐在一张藤椅上,又用白巾抹他的鼻子和嘴唇。
我问道:“你的确记得你的第一次的车票是塞在你的右手的袋里的?”
佩雄道:“是,就是这同一的衣袋。你想这冷冰冰的东西如果早已在我的袋里,我怎么会不觉察?”
“你在电车上可曾遇见熟识的人?”
“没有,一个都没有,这就是最奇怪的一点。”
我低头寻思,又道:“这东西一定是有人放进去的,不足为奇。奇怪的是那人把这断指放在你的袋中,究竞有什么作用?开玩笑?还是要恐吓你?或是——”我说到这里,顿住了说不下去。
我的妻弟接口说:“姊夫,还有什么?你可是说——”我仰起头来,问道:“你有什么意见?”
佩雄疑滞似地说:“晤——这个——这是我个人的私见,对不对,不知道。”
“你姑且说出来听听。”
“姊夫,好几年前,你和霍先生不是破过一个叫做断指团的秘密党的吗?”
我应道:“是。那虽是一个秘密党,不过他们的宗旨并不和一般的匪党相同。”
“不错,我看过你写的那本《断指团》,团党中不设首领,组织上也别开生面。”
“是的。但是自从那年破获以后,这班人至今没有消息。你难道说他们复活了不成?”
“复活不复活,我不知道。但你想他们会不会因着前次的失败,特地来复仇——”我忙摇头答道:“不会。我们当时曾对他们表示过相当的同情。那个执行人樊百平虽给霍桑捉住,但是那是他自投的,后来他好像曾逃出来——”佩雄忙着说:“对了,他既然越狱逃出来,自然要来报复。”
“不。他曾和我们俩握过手,并没有恶感。”
“这也难说。无论如何,他们的团体究竞是被你们俩破的。这一来已尽够有报复的可能。”
我继续反辩。“即使照你的话,他们应当在我和霍桑身上报复,怎么会寻到你身上来?”
话虽不错,但他们谅必知道我是你的亲戚。也许有什么人本要难为你,故而守伏在你家门外。我既然从你家里出来,那人料知必和你有关系,所以就在我身上先下一个警告,你想对不对?”
我仍疑惑地说:“如果如此,我先走出来,他们应当先注意我埃”天气虽不算热。但困惑给予我的烦躁,仿佛加重了我的为酒力所困的脑子的迷糊。我觉得我的额角上有些汗,伸手进白帆布西装的衣袋里去,想取一块手巾。奇怪!有一种冷冰冰湿滋滋的东西接触我的手指。我仔细一摸,不由不直跳起来。
我的衣袋里也有一枚手指!
二、也是一枚断指
惊异吗?自然。我甚至有些恐怖。我强制着把那东西从衣袋里取出来,向桌子上一丢。
真的,是一枚断指!这一枚比佩雄的一枚略为长些,那可憎的颜色是彼此相同的。
佩雄眩目道:“哎哟!越发奇怪了!姊夫,你想我说的党徒们报复的话不是更加近情了吗?”
我不回答,坐下来作迅速的追想。这东西什么时候进我的衣袋的?我从我家里出门时,记得曾摸出这块手巾来用过;上了电车又不曾遇见相识的人。真是太不可思议!
佩雄喘息道:“姊夫,你也是坐电车来的吗?你坐哪一路电车?”
我应道:“我先坐第五路,到了南京路口又改乘第二路。”
雄连连点点头道:“对,对。我也坐过五路电车。一定在这一路车上,有什么人暗中和我们为难。”
又沉吟着不答。办事室中便静寂无声。果真有党徒们报复吗?这难道就算一种警告?
我迫想在电车时的情形。车中很挤轧,有两个人曾贴紧地坐在我的右旁。若说有人乘间把这可憎的东西塞在我的袋里,事实上原是可能的。但这报复的见解究竟太空洞。断指团复活,我怎么事前一些没有风闻?霍桑可已有什么消息?莫非这断指团始终不曾解散,不过在别处活动,我们不知道,现在他们到了上海来,怕我们干涉,又先发制人地向我们警告吗?
砰!前门开动了,又有响亮的皮鞋声音阁阁地直闯进来。是霍桑。
唉,我可以省绞些无谓的脑力了。
霍桑进了办事室的门口,立定向我和佩雄打量,似乎我们俩一起在他的室中是出于他的意外的。
他点点头,含笑道:“什么风把你们俩吹到这里来的?真难得。”
我笑不出,只微微点了点头,依旧坐着。佩雄也扮着鬼脸,静默地瞧他。霍桑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。
他低声问道:“什么事呀?你们俩一块儿来——”佩雄抢口道:“不,我们不是一起来的。霍先生,我们——我们有一件奇怪的事,要等你解决。”
霍桑仍站着。他的锐利的眼光瞧瞧佩雄,又回转来瞧我,一时似也莫名其妙。他的唇吻张动,好像要发问,可是不说出来。忽而他的眼光射到书桌上面,他也不由不失惊诧。
“唉,这两枚断指哪里来的?”
他奔到桌子前,疾忙将两枚手指收起来,丝毫没有怕肮脏的样子。
我乘势答道:“我们正为着这两枚东西要等你来解释。”
霍桑将断指承在他的左掌中,右手早已从他的背后的一只裤袋中摸出一面放大镜来,仔细将断指察验。他的眼光在灼灼地转动,又点点头,分明他已经找出了什么。
他喃喃自语地说:“一枚是食指,一枚是小指。断割的时候血运已经凝结,显见那个人已经死了。哦,指皮枯黯,指甲中留着垢腻,可以推测那人的生前是个苦力。奇怪,包朗,这东西你们到底哪里来的?”
他把断指和放大镜都放在书桌上,沉着地坐下来。我便把佩雄的经历和我们谈论的话一五一十地向霍桑说了一遍。霍桑敛神倾听,术岔口答话。等我说完了,他低垂了头,眼睛凝视在地席上。一回,他才仰起头来,从衣袋中摸出纸烟,擦火烧吸着。
室中又一度静默。佩雄目不转瞬地注视着霍桑。我也不例外。他的有规则的吐烟动作告诉我他的思想机构又在那里工作,而且似乎已有些头绪。
他忽把纸烟从嘴里取下,向我们说:“你们所拟想的这动作出于断指团的报复,的确有几分近情。我这几天得到一种情报,这一班党徒果真有死灰复燃的风闻。”
“唉,真的?”我有些吃惊。
佩雄也抢着问道:“霍先生,这班党徒真有复活的消息?”
霍桑点点头。“真的。不过我只听得他们企图复活,却想不到竟会来向你们寻仇。”
我说:“他们既然要恢复活动,报复的事就算不得希罕。那末我们也应当有个相当的防范。”
霍桑道:“那自然。我总有办法。现在我要问一问。你们对于那个把断指放在你们袋里的人可有些端倪?”
佩雄摇头道:“我一些没有觉察。”
我也说:“这一着真难说。因为我在电车中的时候,除了两个人紧贴在我的右边以外,还有好几个人和我摩肩而过。”
霍桑道:“那末我们姑且假定,这两枚断指,你们都是在五路电车上得到的。”
佩雄点点头。
我答道:“我们起先也这样子推想。”
霍桑道:“既然如此,我们就可更进一步推想。你们俩既然先后出来,虽同样坐过五路电车,但并不是同一部车,这就可知这两枚断指决不是一个人投的。”
“对,很合理。”我应一句。
霍桑继续说:“不过据我观察,那两枚断指似乎是从一个人手上割下来的。这一点倒有些费解。”他斜过目光瞧佩雄,佩雄呆瞪瞪不答。
我说:“我看这不见得难解释。这两枚断指也许真始从一个人手上割下来的,却分派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党徒,以便乘机投放。那两个人势必伏在我家门外,看见我和佩雄先后走出来,他们也就分了两起,跟在我们的后面。等到上了电车,车中乘客拥挤,党人们自然有机可乘了。”
霍桑暗暗点头,似乎赞同我的解释。他又瞧瞧我的妻弟。佩雄还是那么沉默,霍桑又道:“你的理解如果不错,就有一个连带的疑问。假使那复仇的党人果真像你所说的不止一个,或有两个以上,那末他们决不会放弃了我,单单和你们两个为难。我觉得我的寓所门前,不见有什么可疑的人,并且刚才我也坐过电车,我的袋里怎么没——”他说到这里,他的右手不期然而然地伸到他的青哗叽的衣袋中去。一刹那问,他的手突然抽出来,向上一扬,便有什么东西落在书桌上面。他得身体也禁不住直立起来。
霍桑摸出来的竟然也是一枚断指!
三、依样葫芦
这发见太惊人!我诧异得说不出话,连霍桑的不易动摇的定力也几乎保不祝自然,佩雄更感到惊怪。他的静默破坏了,也直立起来。他的惊诧的眼光和霍桑的互相接触了一下,高声喊起来。
“哎哟!霍先生,你——你这一枚哪里来的?”
霍桑不答,楼着身子看那摸出来的手指。那是一枚大拇指,颜色微白,又有些浮肿的样子,和我们俩的两枚不同。霍桑细瞧了一会,忽低声向我们说话。
“这件事弄大哩。你们轻声些。我记得了。当我下电车的时候,果真有个人跟我下车。
现在想起来,那个人的确很可疑。你们等一等,我出去瞧一瞧,外面有没有人埋伏着。”
他蹑足走出去。我和佩雄面面相觑地站着。我看见佩雄的脸色越发惨变,额上的汗在蒸发,连嘴唇上的血色都完全退荆他的嘴唇忽微微颤动,好像要和我说话,但是终于开不出口。我觉得他怪可怜,可是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慰藉的话。
一会,霍桑又轻轻地回进办事室来。
他喘息说:“这屋于外面左边第三棵树和右边第二棵树的背后,各有一个人伏着。若不是今天你们来警告我,我险些儿遭他们的暗算。”
我回答道:“这两个人是断指团团员?”
“当然。”
“他们有什么目的?”
“那是很显明的。他们第一步既已把断指做了警告信,第二步自然要我们的性命;”
佩雄忽失声道:“什么?他们要害我们的性命?”
霍桑作简语道:“那是必然的步骤。”
我看见这孩子着急得厉害,忙辩解道:“这也未必一定如此。铭文,你尽放心。他们如果要伤我们的性命,早就可以下手,何必把这断指来玩什么把戏?”
“姊夫,你——你想他们要怎样对付我们?”
“我料他们的用意至多想恫吓我们,叫我们不要再和他们作对,以便他们可以在上海重新活动。”
霍桑摇头道:“包朗,你别打如意算盘。他们所以用断指做警告信,无非要显示他们的态度光明,要叫我们知道伤害我们的是断指团,不是别人,使我们死一个明白!”
“哎哟!霍先生,现在怎么办?”佩雄的声浪也颤动霍桑仍镇静地说:“那也不用害怕。他们既敢寻上门来,我也决不退缩,少不得要给他们知道些厉害。我——”砰!??椋……两响枪声从窗口里传进来,引起了佩雄的带着哭声的锐呼。
霍桑忙喝令道:“别响!你们快把身子蹲下来!别乱动,也不要声张!”
我慌了,向裤袋中一摸,没有带手枪。霍桑却早已摸出一把手枪,曲着身子,探头向窗外晾望。佩雄蹲伏在一只沙发背后。
砰!??
窗外的枪声又一响。霍桑举起手枪,奔出办事室去。
显然要进击那行刺的匪徒。我正想跟霍桑同出,预备助他一臂,忽被佩雄一把拉祝他喊道:“姑夫,你不要去!这件事怎么——怎么会弄假成真?”
我停了脚步,问道:“哦?弄假成真?你这话什么意思?”
佩雄向书桌上指一指。“这——这两枚手指原是我——我和你开开玩笑的——”我惊怪道:“什么?开玩笑?你——”佩雄扭捏地说:“真的。我告诉你。这两枚东西本是我从校里带出来,乘间把一枚偷放在你的衣袋底里,想和你玩一下子。”
“唉!你这么年纪还是这样子顽皮!”
“昨天晚上有一个叫毕行素的同学,从一个被解剖的尸体上割下了两枚指头,偷放在我的被窝里吓我。我动了好奇心,想跟你和霍先生玩玩。谁知道事情会这么凑巧,竟会弄假成真!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回学校去的。现在这样子,我怎样出去?姊夫,你想我怎么——”霍桑踉跄地回进来,手枪仍拿在他的手里。
我忙问道:“怎么样?”
他说:“匪徒已经逃走了,你们姑且定一定神。”
“你可曾瞧见那发枪的人?”
“瞧见的。我明明看见两个人向东西两面飞奔过去。我防别的树背后也许另有埋伏,我故而不敢深追。”他忽回头瞧高佩雄。“铭文弟,你不是说要回学校去吗?”
佩雄应道:“是。”
“稳妥些,你不如在这里住一夜,等明天再走。”
“不能。我明天一早就有课。”
霍桑略一思索,点点头。“那末不如趁早就走。否则他们如果再来,你出门去,就很危险。”
佩雄疑迟道:“现在就走不会有危险吗?”
霍桑皱皱眉头,答道:“这也难说。晤!我有一个法子。你若是能改装一下,也许可以避免危险。”
“怎么样改装?”
“那只有委屈你一下。”
“晤?”
“把你身上的一套漂亮的西装脱下来,我可以叫施桂借一件旧竹布长衫给你,装做我的仆人模样,他们就不会和你为难。俗语说,‘冤有头,债有主。’他们要向我报复,决不会寻到仆人们身上去。”
佩雄向我瞧瞧,似乎还犹豫不决。我没有表示,心中在责他无事生事,自寻烦恼,但也不便当场斥责他。
霍桑又说:“铭文弟,你如果愿意屈一屈身分,尽管放心出去,我担保你没有危险。
但是你得立刻就行,再迟我也保不祝”局势压迫佩雄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他心虽不愿,却势在必行。五分钟后,他穿上了施挂的一件褪了色的旧竹布长衫,偷偷掩掩地走出去。
霍桑目送他走出了大门、回到室中,重新烧了一只纸烟,默默地坐着吸烟,似乎他正在寻思什么抵敌的方法。我想起了佩雄所说的弄假成真的话。
我说:“霍桑,这件事真可算得再凑巧没有。你还不知道我和佩雄袋中的两枚断指就是他——”霍桑突淮笊?溃骸鞍?剩?憬裉旌攘硕嗌倬疲靠墒腔姑挥行淹福俊? 我怔了一怔,呆瞧着他,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。
霍桑继续道:“你自己上了这孩子的当,难道想连我也睡在鼓中?”
我惊喜道:“喔,你早已瞧破了他的把戏?”
霍桑吐一口烟。“自然。你想他的故事既然如此诡诞不经,说话时的状态又明明带着假面,他又是个善于和人家开玩笑的孩子。你实在太糊涂哩!”
我涨红了脸,答道:“我起先本也有些疑心,可是他的表演工夫真不坏,不知怎的,我竞被他诱进了迷阵。”
霍桑笑一笑。“晤,我知道的。你的观察力虽不见得十二分高妙,但今天你若不是多喝几杯酒,那也决不会轻轻地被他瞒过。”
“那末你在什么时候才瞧破的?”
“当他进这里来时,我恰巧回来,就在他的后面。我见了他的鬼鬼祟祟的状态,就不禁引起疑心。后来你和他的谈话,我完全听得。我知道他的玩笑的对象不单是你,连我也在内。所以我就利用他的方法,依样葫芦地和他了一下子。谁知他太不中用,不耐玩,几乎要哭出哩。”
我坐直了些,张目道:“什么?后来的事是你假意播弄的?”
霍桑努力呼吸了几口烟,点点头。“包朗,你真太老实哩。你看见了我刚才的说话和举动,难道还辨不出真假?”
我的颊上有些发热,答道:“虽然,但是你的衣袋中的那枚手指,还有窗外的三次枪声——”霍桑忽把书桌上的小铃按一按。施桂应声走进来。他的脸上带着笑容,手中执着两支打火药纸的假手枪,走过来把枪放在书桌上。
霍桑含笑说:“施桂,今天你扮演一个配角,着实玩得不错。……喂,你把桌上的一枚大拇指重新放到化验室的仿墨林瓶里去。这是我们那年从南京带回来的纪念品,不能失掉。……慢,还有两枚手指,你也一起保存了,免得丢在外面,再引起人家的惊疑。”
施桂答应了,取了三枚断指退出去。他正走到门口,霍桑又叫住他。
“施桂,等一会你把这一身衣服送到肋板广桥上海医专去。”
施桂退出去后,霍桑丢了烟尾,开了抽屉,取出一套信笺信封。他先开了信封,又在信笺上写了几句。
他向我说:“这孩子虽喜欢胡闹,胆子究竟还校要是我不马上说明白,他今夜里一定睡不着。如果让尊夫人知道了,伊疼惜弟弟,不免要说我恶作剧了。”
他格格地笑了一笑,随手将写好的信笺递给我。我接过来默念。
那短信道:
“小孩子:
今天的事大概足够给你上一课吧?你若要打破这小小的疑团,不妨就问问这送衣的人。
霍桑”
|
|